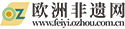叶长青听到门响,握紧筷子,合上眼,屏息凝神,只待那人靠近就一筷子戳瞎他的眼睛。
木屐的声音一下一下敲着他的耳膜,再近一点,他握得更紧了,再近一点,那人衣服发出的窸窣声越来越清晰,呼吸打在他脸上,叶长青瞬间怒目圆睁,一筷子就要戳穿这人的脑袋,却不料手臂突然僵住,想是多日不动弹,猛地发力伤到筋了,那人吓得叫了一声,竟是个女孩的声音。
叶长青警觉地看着她,“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女孩被吓得花容失色,战战兢兢走到他面前,她穿一件白底紫里织有花鸟图案的小袖,很衬她白皙的皮肤,脸上敷了厚厚的粉,不,确切的说脖子上也敷了粉,眉毛被剃过,用墨在原处描上淡细的眉状,嘴巴涂得红艳艳的,她见叶长青看她看呆了,不好意思的咧嘴一笑,露出两排黑齿,像开了口的墓穴,叶长青毛骨悚然。
他心说,这女孩估计也是个受害者,多漂亮的女孩啊,被这伙儿倭人给弄成这幅鬼样子了,他惊吓之余回过神来,态度和缓了不少。
女孩跪坐在他面前,连着鞠了三个躬,依然是那种没有高低起伏的语调,“对不起,对不起,惊扰到您了,真是对不起。”
原来是个倭人,叶长青复又双眉倒竖,“你到底是什么人!”
“对不起,”她见叶长青发火,弯下小巧的身子又是一鞠躬,“我是小林龙马的妹妹,小林千夏。”
叶长青一只手实在是撑不起自己半个身子了,咣当一下贴到地上,虚弱的喘着气,“你们为什么要折磨我?是因为我杀了倭寇,你们要替同胞报仇?”
千夏听到这儿圆圆的眉毛凑到一起,略带愤恨的说道,“阁下实在是太无礼了,怎么能把小林一族跟强盗摆放在一起,”她意识到自己有点凶了,调整了下语气,“我们小林家可是从镰仓幕府时代绵延至今的名门大族,能跟小林家相提并论的也就只有佐竹氏、最上氏、毛利氏、小早川氏与岛津氏······”
“我干你老母!”叶长青懒得听他报菜名一样自报家谱,“你们要捉我去哪儿?”
千夏见他龇牙咧嘴,白了他一眼,“哼,都被打成这样了还这么嚣张,阁下的火气可真大呢。”
“你们脑子都被门挤了吧!你们一家人都是疯子吗!”尽管已经筋疲力竭,叶长青还是扯着嗓子叫道。
“早知道就不该给你做鳗鱼饭吃,吃饱了就冲我嚷嚷,就应该让十兵卫与佐佐木每天都揍你一顿,”千夏立起身子,整了整衣带,瞥了眼躺在地上气若游丝却怒气冲冲的叶长青,“算了,看你这幅尊容,我就宽恕你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叶长青痰喘着吼道,“我恨不得将你们这些倭人食肉寝皮、敲骨吸髓,我······”他还想再多说一些狠话,却咯血数口。
千夏赶紧从袖子里掏出绣有樱花的手绢擦他的嘴角,“你别说话了,你需要静养。”
叶长青耳朵里像是有一千只喝醉了的蜜蜂在跳着群舞,脑壳嗡嗡嗡叫唤的快要跟脸皮分家了,千夏晃成好几个影儿,他想推开千夏,却连这最后的一丝气力都荡然无存,竟晕厥了过去。
这时,舱门开了。
小林龙马双臂抱肩踱着步子走了进来,“这位少年的忍耐力可真是惊人,连番殴打,羞辱谩骂,一般人不出三天便崩溃了,他竟能忍受五天之久,而且丝毫看不出精神被击溃的迹象,我没有看走眼,重振幕府权威,刺杀叛乱大名的任务交给他一个生脸最合适。”
千夏把叶长青的脑袋轻轻放到地板上,困惑的看着哥哥,“可是,他又不会任何武术,那些叛乱的大名手下全是剑术高手,只怕他还没近前就被斩落人头了。”
“不会可以学,”小林走近昏倒在地的叶长青,低头端详着他铺满煞气的脸,“我看中的是他这个人,伊贺国上忍服部正康可以帮助小林家把他训练成一名武功盖世的忍者,届时羽田波旬就算被剑术高手层层护卫,迟早也要被摘去项上人头。”
“可是哥哥,”千夏将心中的疑问和盘托出,“波旬公布武天下,各路大名纷纷俯首帖耳,日本怕是要在波旬公手里天下一统,除去波旬公,日本将重新陷入四分五裂,而幕府软弱无能,为何小林家非要······”
“八嘎!”小林眼珠都要努出来了,“小林家世受将军恩泽,没有历代将军就没有小林家的今天,羽田波旬就是个乱臣贼子,整日将‘夺取天下’挂在嘴上,安心呆在尾张国老死算了,真是个疯子。”
千夏不敢再顶撞哥哥,她知道哥哥的脾气,恭敬地趋步倒退出了船舱。
“今儿也不早了,封兄,我实在是太困了,”周桐打了个长长的哈欠,眼屎堆在眼角被挤成两条线,“咱儿凑空接着唠吧。”
封居胥听得兴味正浓,见周桐意兴阑珊,也只好说,“行,周兄先歇息,得意浓时便可休嘛,一下子全讲完,明儿没得听了。”
封居胥告别了周桐,回到自己厢房,他躺在床上,心里还在想着叶长青的故事,他分明就是罗什寺塔第四层长卷中人物,想到他最后僵挺在地,眼球遍布血丝,手筋脚筋从皮里爆了出来还翻着卷儿,嘴巴张的老大的那副惨相,封居胥不觉叹了口气,他自己虽然怂,可架不住崇拜当世英雄,所谓缺啥补啥吧。
物伤其类,兔死狐悲,他由叶长青想到周桐,又想到来军,三人均是暴毙而亡,自己与他们的画像同在一塔之内,是否······
他突然吓得浑身直哆嗦,自己长这么大,连个女人都没睡过,窝窝囊囊活了这么久,最后落得个不得好死,他虽然想往好的方面想——可能也就他们三个人比较倒霉,自己嘛,最后肯定是白日飞升,长生不死了。
他不断地自言自语,说自己早已被神仙点选,肯定不会暴毙而亡,可一想到来军有两个神仙护佑,依然喋血青山之前,不免泄了气,眼泪从眼角淌了下来,他根本控制不住这决堤的洪水,窗外的宝塔悄然矗立,无声的时间默然冲刷着世间的痛苦。
不行,不能就这么束手就擒,封居胥一锤床板,他麻溜的穿好衣服,朝着宝塔小跑而去。
塔门洞开,他壮着胆咬着牙冲了进去,门歘的一声自动关上了。
有了上一次入塔的经验,他不是那么害怕了,一溜烟跑到二楼,佛龛跟上次一样一路照着他登塔的路,他从怀中掏出了笔,既然孙悟空可以改《生死簿》,那我为什么不能将长卷连同上面的判词一笔抹消呢!
可走进一瞧,他傻了眼,上面画了个女孩,高高的密笼笼的发髻,紧贴瓜子脸的水鬓,如石榴一般嫣红可爱的嘴唇,脖子上围了一条藏青色手帕,上穿一件黑底洒红花的无袖长衫,下着缀以圆花方块的血色罗裙······不用看了,这不就是吕瑶儿嘛,旁缀一首曲子词:
“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着饯行杯,眼阁着别离泪。刚道得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
这是说早晚要跟我分别吗?封居胥突然有点黯然神伤,他知道吕瑶儿看不上他,看到这首曲子词不觉胸闷,算了,人家本来也没把我当回事,曲子里都说有别离泪,人家肯为我哭一场,也算没白活吧,不对,或许是自己给她哭了一场,以吕瑶儿的性子,她才不会为自己哭呢。
封居胥握着毛笔的手在抖,他想把整幅画都给画满叉,可又觉得画了叉能怎样?吕瑶儿就喜欢自己了?
封居胥啊封居胥,你也太自作多情了,他把毛笔往地上一摔,溅了自己一脚墨汁,有气无力的往三楼拾级而上。
他走近三楼的画卷,上面竟不是周桐,还是一位女子,看来整座塔的画卷都换过了,而且原先是讲述一个人一生的长卷,如今变成了单幅画卷,只有美女跟曲子词。
他凑近仔细端详,这女子头上挽着发髻,没吕瑶儿那么高,着一件四面做成如意云头形的云肩,交领上衣,两条长袖,下着一条粉色长裙,束在上衣之外,腰部又围了一条白色短裙,一条绿色丝带束腰,余端系成花结,垂于身侧,一条长而柔软的披帛搭在两肩。
画中人一副闷闷不乐的神态,眼角低垂似是在生谁的气,封居胥心说,这女孩长得好可爱啊,急忙去看旁边的曲子词:
“青苔古木萧萧,苍云秋水迢迢。红叶山斋小小。有谁曾到?探梅人过溪桥。”
看来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冷美人,他又把那张色脸凑近画中人仔细看了一遍,越看越耐看,方才的难受劲儿早就丢到爪哇国了。
上面肯定还有,他乐呵呵的往楼上跑去。